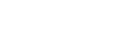《旧唐书》斠补举例——以《太平御览》引《唐书》为中心(一)(一)
详细内容
《太平御览》(以下简称《御览》)是考订《旧唐书》的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由于《御览》引《唐书》的内容大多与《旧唐书》出于同一史源,《旧唐书》中的许多错误,都可以根据《御览》的记载加以校订[1]。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御览》引《唐书》与《旧唐书》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错误或模糊的认识,受传统观点的影响,人们往往只是将《唐书》看作《御览》摘引自《旧唐书》的内容,迄今为止,尚未对《御览》引《唐书》进行科学整理[2],既影响了对《御览》引《唐书》的史料价值的认识,也使得《旧唐书》中一些明显的失误长期没能得到纠正。
我们在系统辑录、整理见于《御览》的《唐书》资料的基础上,将《御览》引《唐书》的内容逐条与《旧唐书》进行了比勘,发现了许多可以利用《御览》加以考订的《旧唐书》的错误,本文拟将其中涉及到史实判断或文义理解的错误分为四种类型举例讨论:第一类属于前人及时贤没有注意到的,可以利用《御览》引《唐书》加以考订的《旧唐书》的失误。第二类属于前人已经注意,但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的《旧唐书》的错误。第三种情况是前人根据《御览》的记载,已经对《旧唐书》的错误进行了正确的考订,但是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仍然延续了原有错误,没有吸纳有关的校勘或研究成果[3]。此外,在编纂《新唐书》及《通鉴》等史书时,曾大量参考和利用了《旧唐书》的资料[4],而《旧唐书》的错误也影响了这些史籍的内容,通过寻绎《御览》的有关记载,对这类失误也可以加以订正。本文将分为四节对以上四类情况分别加以探讨,通过讨论,希望能引起或加深对《御览》引《唐书》史料价值的认识,同时对《旧唐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有所助益。
这里还要强调的一点是,除了第三节点校本失收前人校勘成果诸条外,第一、二、四节讨论的《旧唐书》的失误,在点校本中也全都未出校记。也就是说,本文涉及的所有条目都属于中华书局点校本失校或误校的内容,正文中对此不再具体说明。
一
自清代以来,学术界对《旧唐书》已经做了大量的校勘和考订工作,并由中华书局组织人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点校本,对研读和利用《旧唐书》的资料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由于对《御览》引《唐书》的史料价值认识不足,在以往的整理工作中也遗漏了不少可以利用《御览》加以纠正的错误,试举证如下。
1. 卷二《太宗本纪》上,1/22[5]
太宗自南原率二骑驰下峻坂,冲断其军,引兵奋击,贼众大败,各舍杖而走。
仅以二骑何以能“冲断”敌军,事颇可疑。《御览》卷三一一(2/1432)[6]称:“太宗自南原遥见尘起,知义师退,率二百骑驰下峻坂,杀一贼将,遂冲断其军,出于阵后,表里齐噪,响若崩山,隋师大溃,各舍杖而走。”《册府》卷七亦作“二百”。本段与《旧唐书》史源相同,但记述详尽,文意完足。当以《御览》“二百”为是,《旧唐书》“二”下夺“百”字。
2. 卷三《太宗本纪》下,1/54
丁卯,宴武功士女于庆善宫南门。酒酣,上与父老等涕泣论旧事,老人等递起为舞,争上万岁寿,上各尽一杯。
“万岁寿”,《御览》卷一○九(1/526)作“千万岁寿”。今按,“千万岁寿”是唐人上寿祝酒习用语,如裴度在朝廷宴会上为宪宗祝酒庆寿称“愿与四海九州之人,同上千万岁寿。”[7]《旧唐书》卷一《高祖纪》高祖宴西突厥使,长孙无忌“上千万岁寿”,卷一○《肃宗纪》肃宗即位灵武,裴冕跪称“臣稽首上千万岁寿。”都是显例。在时人诗文中,也屡见“千万岁寿”的祝词,鲜见“万岁寿”的史例。如李贺《拂舞歌辞》“樽有乌程酒,劝君千万寿。”[8]沈佺期《岁夜安乐公主满月侍宴》“圣皇千万寿,垂晓御楼开。”[9]刘禹锡《汉南书事》“陛下好生千万寿,玉楼长御白云杯。”[10]元稹《和乐天初授户曹喜而言志》“各称千万寿,共饮三四巡。”[11]萧至忠在重阳节所作应制诗中也有“重阳千万寿,率舞颂升平”的描写[12],此类例证甚颗,不赘举。当从《御览》,《太宗本纪》“万”上夺 “千”字。
3. 卷八《玄宗本纪》上,1/166
分遣万骑往玄武门杀羽林将军韦播、高嵩,持首而至,众欢叫大集。
《御览》卷一一一(1/533)称:“分遣万骑往玄武门杀羽林将军韦璇、韦播、高嵩,持首而至,众欢叫大集。”《通鉴》卷二○九景云元年正作“斩韦璇、韦播、高嵩以循”。《旧唐书》当漏书“韦璇”。
4. 卷八《玄宗本纪》上,1/168
延和元年六月,凶党因术人闻睿宗曰:“据玄象,帝座及前星有灾,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更居东宫矣。”睿宗曰:“传德避灾,吾意决矣。”
凶党因术人闻睿宗,《御览》卷一一一(1/533)“闻”作“间”。据上下文,术人所进,显系离间之语,当以《御览》“间”字为是,疑《旧唐书》因形近而误“间”为“闻”。
5. 卷九《玄宗本纪》下,1/234
明年九月,郭子仪收复两京。十月,肃宗遣中使啖廷瑶入蜀奉迎。丁卯,上皇发蜀郡。
收复两京,《御览》卷一一一(1/536)“两”作“西”。今按,此“明年九月”,即唐肃宗至德二载九月。据《旧唐书》卷一○《肃宗本纪》及《通鉴》卷二二○记载,至德二年九月癸卯,唐军克西京;甲辰,遣啖廷瑶入蜀奏捷;十月丁未,啖廷瑶至蜀;而克东都则更在十月壬戌。肃宗遣啖廷瑶入蜀在收复西京之后,攻克东都之前,当从《御览》作“西京”,《旧唐书》“两京”之“两”,是“西”之讹字。又,十月为啖廷瑶抵蜀的时间,《旧唐书》及《御览》均称十月遣入蜀,亦不确。
6. 卷一○《肃宗本纪》,1/255
两省官十日一上封事。
本条《御览》卷二二三(2/1066)作:“干元二年四月,两省谏官十日一上封事。”《唐会要》卷五五“谏议大夫”亦称:“干元二年四月四日敕。两省谏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论得失,无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劝。”《旧唐书》“两省”下应夺“谏”字[13]。
7. 卷一一《代宗本纪》,2/279
时怀恩诱吐蕃数十万寇邠州,客将尚品息赞磨、尚悉东赞等寇奉天、醴泉……
客将,《御览》卷一一二(1/544)及《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作“蕃将”。当从《御览》,《旧唐书》“客”为“蕃”之讹文。
8. 卷一二《德宗本纪》上,2/336
丙子,哥舒曜进军至颍桥,大震雷,人死者十之三四,乃退保襄城。
因震雷而死者“十之三四”,事殊可疑。《御览》卷三二九(2/1512)记此事称:“哥舒曜欲攻李希烈于许州,师次颍桥,大电雷而雨,营中震不能言者三四十人,驴马死者有七。曜恶之,乃退。”揆诸事理,当从《御览》,《旧唐书》“十之三四”应作“三四十人”,且诸人只是“震不能言”,并非震死。《旧唐书》误。又,《册府》卷四○○称:“营中震不能言者三四千人”,“千”疑为“十”之误。
9. 卷一三《德宗本纪》下,2/385
夏四月壬戌,上幸兴庆宫龙堂祈雨。乙丑,大雪。
祈雨得雪,事属可怪。《御览》卷九二五(4/4111)详载此事本末:“贞元十三年四月,上以自春已来,时雨未降,正阳之月,可行雩祀。遂幸兴庆宫龙堂,兆庶祈祷。忽有白鸬鹚沉浮水际,群类翼从其后,左右侍卫者咸惊异之。俄然,莫知所往,方悟龙神之变化,遂相率蹈舞称庆。至乙丑,果大雨,远近滂沱,于是宰臣等上表陈贺。”《唐会要》卷二二“龙池坛”与本条内容相同,亦作“后大雨果下。”《旧唐书》“大雪”之“雪”当为“雨”之讹文。
10. 卷一五《宪宗本纪》下,2/447
以前朔方灵盐节度使王佖为右卫将军。将相出入,翰林草制,谓之白麻。至佖,奏罢中书草制,因为例也。
本条“至佖”以下,文意几不可解。《御览》卷一一四(1/552)记此事称:“元和中,以前灵盐等节度使王佖为右卫将军。佖在镇无智略以驭下,居常猜忌,及多杀人以惧之,众益不附。乃召至,逾月而授以[右]卫将军。凡将相出入,皆翰林草制,谓之白麻,佖始以责罢,中书草制。”《新唐书》卷一五四《王佖传》亦正作“至佖,以责罢,遂中书进制。”当从《御览》,《旧唐书》“奏罢”之“奏”应为“责”之讹文,标点亦连带而误,应正作“至佖责罢,中书草制,因为例也。”[14]
11. 卷一五《宪宗本纪》下,2/466
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诣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
乃送诣寺,“送诣”文意略嫌重复。殿本与点校本同,百衲本作“乃送诸寺”。今按,《御览》卷六五四(3/2923)本条作“乃送诸寺”。《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亦作“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且在韩愈上疏中,也有“令诸寺递迎供养”、“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等语,可知诸本“诣”必为“诸”之形讹。又,“舍施”不词,《御览》作“施舍”,或《旧唐书》为倒文。
12. 卷一七下《文宗本纪》下,2/575-576
十一月乙卯朔,是夜,彗孛东西竟天。壬戌,诏曰:“……当求衣之时,睹垂象之变,兢惧惕厉,若蹈泉谷。是用举成汤之六事,念宋景之一言,详求谴告之端,采听销禳之术……”
详求谴告之端,文意欠安。《御览》卷一一五(1/558)作“详求谴咎之端”,《册府》卷九一亦作“谴咎”,《旧唐书》之“告”当为“咎”之讹字。
13. 卷一八上《武宗本纪》上,2/587
五月辛未,中书门下奏:“据《六典》,隋置谏议大夫七人,从四品上……此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则敬其言而行其道。况蹇谔之地,宜老成之人,秩未优崇,则难用耆德。其谏议大夫望依隋氏旧制,升为从四品……
“故其秩峻,其任重,则敬其言而行其道”句,文气未顺。《御览》卷一一五(1/558)“敬”上有“君”字。今按,宰臣议论的主旨是认为谏议大夫任重而秩卑,难以起到辅佐君主、补过拾遗的作用,应该委以峻秩重任,才能得到君主的敬信。当以《御览》为是,《旧唐书》“则”下脱漏了关键的“君”字。又,“蹇谔”不词,《御览》作“謇谔”,《旧唐书》因“謇”、“蹇”形近而误。
14. 卷一八上《武宗本纪》上,2/604-605
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寺并废。
《御览》卷六五八(3/2940)作“上州各留寺一所,中、下州寺并废。”今按,既有上、下州,则不应不及中州,当以《御览》“中、下州”为是,疑《旧唐书》漏书“中”字。
又,《唐会要》卷四八“寺”亦载此事称:“中书门下奏,天下诸州府寺,据令式,上州以上,并合国忌日集官吏行香。臣等商量,上州已上合行香州,各留寺一所,充国忌日行香,列圣真容,便移入合留寺中,其下州寺并合废毁。”参照《御览》判断,疑《唐会要》“便移入合留寺中”之“中”与下文“其”字互倒,原文似应作“便移入合留寺。其中、下州寺并合废毁。”所谓“并合废毁”,就是指“中、下州”言。《旧唐书》的编者很可能是以“寺中”不文,在倒文的基础上,将“中”妄改为“内”。
15. 卷一八下《宣宗本纪》,2/617
二月丁酉,礼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进士三十三人,其封彦卿、崔琢、郑延休等三人,实有词艺,为时所知,皆以父兄见居重任,不得令中选。”诏令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韦琮重考覆,敕曰:“彦卿等所试文字,并合度程,可放及第……”
三十三人,《御览》卷六二九(3/2819)作“二十三人”,《唐会要》卷七六“进士”、《册府》卷六四一、《登科记考》卷二二俱同《御览》,《旧唐书》“二十三”当误。
又,“不得令中选”,与上下文意不合,《御览》、《唐会要》、《册府》作“不敢选”,《登科记考》作“不敢令中选”,当从《御览》及诸书,《旧唐书》“不得令中选”之“得”,当是“敢”之讹字。
又,“并合度程”,《御览》、《唐会要》、《册府》俱作“尽合程度”,《登科记考》同《旧唐书》。今按,“度程”语涉生僻,疑应从《御览》及诸书作“程度”,《旧唐书》及《登科记考》之“度程”或为倒文。
16. 卷一九上《懿宗纪》,3/677
《语》曰: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
即,《御览》卷一一五(1/561)作“则”。《论语·子张》正作“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旧唐书》之“即”应为“则”之形讹。
17. 卷二一《礼仪志》一,3/817
今案封禅者,本以成功告于上帝。天道贵质,故藉用稿秸,樽以瓦甒。此法不在经诰,又乖醇素之道,定议除之。近又案梁甫是梁阴,代设坛于山上,乃乖处阴之义。今定禅礼改坛位于山北。
“近又案梁甫是梁阴,代设坛于山上”句,殊难索解。《御览》卷五三六(3/2432)作“按梁甫是谓梁阴,近代设坛于山下[上],乃乖处阴之义。”《通典》卷五四亦称:“又按,梁甫是谓梁阴,近代设坛于山上,乃乖处阴之义。”百衲本及殿本均正作“又案,梁甫是梁阴,近代设坛于山上”,点校本“近”字为误植,应移置于下文“代设”句前。
又,《旧唐书》诸本“梁甫是梁阴” 文理欠通。当从《御览》及《通典》“梁甫是谓梁阴”,《旧唐书》夺“谓”字。
18. 卷二四《礼仪志》四,3/914
开元二十六年,玄宗命太常卿韦绦每月进《月令》一篇。是后每孟月视日,玄宗御宣政殿,侧置一榻,东面置案,令韦绦坐而读之。
孟月视日,义不可解。《御览》卷七○六(3/3147)“视”作“朔”。《唐会要》卷二六“读时令”与《御览》同。当从《御览》,《旧唐书》“视”显为“朔”之讹字。
19. 卷三七《五行志》,4/1368
调露元年,突厥温傅等未叛时,有鸣鵽群飞入塞,相继蔽野,边人相惊曰:“突厥雀南飞,突厥犯塞之兆也。”
前云“鸣鵽”, 后称“突厥雀”,上下文意不相属。《御览》卷九二三(4/4099)称:“初,突厥之未叛也,有鸣鵽群飞入塞,相继蔽野,边人相惊曰:‘此鸟一名突厥雀,南飞,突厥入塞之候也。’”《唐会要》卷四○“杂灾变”与《御览》同,《旧唐书》“突厥雀”前疑当补“此鸟一名”数字[15]。
20. 卷四二《职官志》,6/1786-1787
龙朔二年二月甲子,改百司及官名……詹事为端尹府……
今按,詹事为官名,端尹府为衙署名,以“詹事为端尹府”,文理不通。《御览》卷二四五(2/1159)称:“龙朔二年,改詹事为端尹,詹事府为端尹府。”《通典》卷三○与《御览》完全相同[16]。当从《御览》,《旧唐书》本文“改詹事为”之下当误夺“端尹詹事府为”六字。
21. 卷四八《食货志》,6/2095
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
“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御览》卷八三六(4/3732)作“其字合[含]八分及篆、隶三体。”《唐会要》卷八九“泉货”亦称:“其字含八分及篆、隶三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亦称“其文以八分、篆、隶三体”。当从《御览》及诸书,《旧唐书》本条显有夺文[17]。
22. 卷五○《刑法志》,6/2133-2134
高祖初起义师于太原,即布宽大之令……又制五十三条格,务在宽简,取便于时。
“务在宽简”,语义未安。《御览》卷六三八(3/2856)作“务存宽简”。《通典》卷一七○与《御览》同,《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作“务从宽简”,与《御览》文义略同。当从《御览》,《旧唐书》“在”为“存”之形讹。
23. 卷五四《王世充传》,7/2233
八月,秦王陈兵于青城宫,世充悉兵来拒,隔涧而言……太宗谓曰:“四海之内,皆承正朔,唯公执迷,独阻声教。东都士庶,亟请王师,关中义勇,感恩致力……
感恩致力,《御览》卷一○七(1/516)作“咸思致力”,较《旧唐书》文义为长。“感恩”、“咸思”字形相近,颇易讹误,如《旧唐书》卷一四四《杜希全传》引德宗《君臣箴》有“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语[18],《唐会要》卷七三“灵州都督府”便误作“感恩正直”。疑《王世充传》“感恩”亦为“咸思”之形讹[19]。
24. 卷五四《窦建德传》,7/2235
县以安祖骁勇,亦选在行中,安祖辞贫,白言漳南令,令怒笞之。
白言漳南令,“白言”嫌语义重复。《御览》卷一○七(1/517)作“自言于漳南令”,较“白言”文义为长。疑《旧唐书》之“白言”为“自言”之形讹。
25. 卷五九《许钦明传》,7/2329
万岁通天元年,授金紫光禄大夫、凉州都督。钦明尝出按部,突厥默啜率众数万奄至城下,钦明拒战久之,力屈被执。
《御览》卷八四二(4/3764)本条云:“凉州都督计[许]钦明尝出按部,有吐蕃数万奄至城下,钦明拒战久之,力屈被执。”一作“突厥默啜”,一作“吐蕃”。岑仲勉先生曾引《通典》“西戎序略”、“吐蕃传”,《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吐蕃传”,《新唐书》“则天皇后纪”、“吐蕃传”等多种记载,证明本年进犯凉州者实为吐蕃[20],但失引《御览》本条非常关键的记载。《旧唐书》本条与《御览》同源,惟改“吐蕃”为“突厥默啜”,非是。
26. 卷五九《许钦明传》,7/2329
贼将钦明至灵州城下,令说城中早降,钦明大呼曰:“贼中都无饮食,城内有美酱乞二升,粱米乞二斗,墨乞一梃。”是时,贼营处四面阻泥河,惟有一路得入,钦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简兵陈将,候夜掩袭,城中无悟其旨者,寻遇害。
简兵陈将,文意欠通。《御览》卷八四二(4/3764)作“冀有[其]简兵练将,候夜掩袭”《册府》卷四二五亦称“冀其拣兵练将,候夜掩袭”。《新唐书》卷九○《许钦明传》称:“钦明欲选将柬兵,乘夜袭贼也。”《通鉴》卷二○六神功元年作“意欲城中选良将、引精兵,夜袭虏营。”参照诸书,当以《御览》及诸书“简兵练将”为是,《旧唐书》之“陈”应为“练”之讹字。
27. 卷六三《封伦传》,7/2395
开皇末,江南作乱,内史令杨素往征之,署为行军记室。船至海曲,素召之,伦坠于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见,竟寝不言。
《御览》卷三九六(2/1828)“召”上有“夜”字。今按,唯有“夜召”,下文“竟寝不言”始有着落。《旧唐书》当夺“夜”字。
28. 卷六七《李靖传》,8/2479
其年二月,太宗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慰谕,靖揣知其意,谓将军张公谨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遂选精骑一万,齎二十日粮,引兵自白道袭之。”公谨曰:“诏许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讨击。”
“引兵自白道袭之”句,文气未尽。《御览》卷三一六(2/1457)本条亦载李靖语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齎二十日粮,引兵自白道袭之,破虏必矣。”《通鉴》卷一九三称:“若选精骑一万,齎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正与《御览》同义。《旧唐书》本条当应从《御览》增补“破虏必矣”四字,文意始称完足。又,《旧唐书》“遂选精骑一万”,《御览》及《通鉴》“遂”作“若”,两相比较,亦以《御览》文意为长。
29. 卷六七《李靖传》,8/2481
太宗将伐辽东,召靖入阁……对曰:“臣往者凭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残年朽骨,唯拟此行。陛下若不弃,老臣病期瘳矣。”太宗愍其羸老,不许。
“老臣病期瘳矣”句,语意未安。《御览》卷二八三(2/1770)作“老臣病其瘳矣”,《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作“病且瘳矣”,与《御览》文义略同。《旧唐书》之“期”当为“其”之误字。
30. 卷七一《魏征传》,8/2549
是月,长乐公主将出降,帝以皇后所生,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征曰:“不可……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子为公主。既加‘长’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相逾越。”
“子为公主”,与前文“天子姊妹为长公主”殊不相类。《御览》卷一五四(1/749)作“天子之女为公主”,《贞观政要》卷五亦称“天子之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当以《御览》为是,《旧唐书》误。
31. 卷七九《祖孝孙传》,8/2709
又祖述沉重,依淮南本数,用京房旧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为一部,以律数为母,以一中气所有日为子,以母命子,随所多少,分直一岁,以配七音,起于冬至。
以律数为母以一中气所有日为子,《御览》卷五六四(3/2550)作:“以律数为母,以气候为子,以一中气所有,以日为子”,详绎文意,《旧唐书》“以律数为母”下夺“以气候为子”五字,又复在“日”上夺“以”字。
32. 卷八五《唐临传》,9/2812
高宗尝问临在狱系囚之数,临对诏称旨,帝喜曰:“……然为国之要,在于刑法。法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务令折中,称朕意焉。”
《御览》卷二三一(2/1097)本条作:“高宗问大理唐临狱系囚之数,临对曰:‘见囚五十余人,唯二人合死。’上闻囚数不多,怡然形于颜色,谓临曰……然为国之要,在于刑法。刑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务令折中,称朕意焉。”稍事比较可知,二书史源相同,且《御览》所引详于《旧唐书》。“法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御览》前“法”作“刑”。今按,揆诸文意,上文称治国之要在刑法,下文分述刑、法,“刑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文从字顺,层次分明。当从《御览》,《旧唐书》前“法”应为“刑”之误。
33. 卷九一《袁恕己传》,9/2943
后与敬晖等累遭贬黜,流于环州。寻为周利贞所逼,饮野葛汁数升,恕己常服黄金,饮毒发,愤闷,以手掘地,取土而食,爪甲殆尽,竟不死,乃击杀之。
何以“饮毒发”而食毒人竟尔不绝,必待击杀方死,殊难索解。《御览》卷九九○(4/4381)云:“袁恕己与敬晖等累被贬黜,流于环州。寻周利用[贞]左右逼令饮野葛汁数升,不死。因击杀之。恕己素服黄金,故毒药不发。”原来是因为袁恕己常服食黄金,使野葛汁的毒性无法发作,故尔不死,最终不得已而“击杀之”。文中所述掘地、食土等诸种“愤闷”情状,也都是因“饮毒不发”而致。当从《御览》,点校本《旧唐书》“饮毒发”[21]之“发”上误夺“不”字,遂使文义扞格不通[22]。
34. 卷一○五《杨慎矜传》,10/3225
时太平且久,御府财物山积,以为经杨卿者,无不精好,每岁勾剥省便出钱数百万贯。
太平且久,《御览》卷二三二(2/1104)“且”作“日”。当以《御览》文意为长,《旧唐书》“且”应为“日”之讹文。
35. 卷一一八《元载传》,10/3411
又于近郊起亭榭,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于宿设,储不改供。
皆于宿设,文义殊嫌含混。《御览》卷四九三(3/2257)作“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如宿设,储不改供。”“皆如宿设”,文意较“皆于宿设”为长。《新唐书》卷一四五《元载传》称:“近郊作观榭,帐帟什器,不徙而供。”正与《御览》同义。当从《御览》,疑《旧唐书》“皆于宿设”之“于”应为“如”之误字。
36. 卷一一八《王缙传》,10/3418
又设高祖已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
《御览》卷三二(1/152)与本条完全相同,唯“舁出内”下多一“庭”字。 《新唐书》卷一四五《王缙传》:“设高祖已下七圣位,幡节、衣冠皆具,各以帝号识其幡,自禁内分诣道佛祠。”“禁内”与“内庭”同义。当以《御览》文意更为完足,《旧唐书》“内”下应据补“庭”字。
37. 卷一一九《杨绾传》,10/3434
今欲依古制乡举里选,犹恐取士之未尽也,请兼广学校,以弘训诱。
取士之未尽,《御览》卷六二九(3/2817)作“取士之道未尽”。《唐会要》卷七六“孝廉举”亦作“今依古制,恐取士之道未尽。”当从《御览》,《旧唐书》“之”下夺“道”字。
38. 卷一三○《李泌传》,11/3623
初,肃宗重阴阳祠祝之说,用妖人王玙为宰相,或命巫媪乘驿行郡县以为厌胜。凡有所兴造功役,动牵禁忌。而黎干用左道位至尹京。尝内集众工,编刺珠绣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为禳禬,且无虚月。德宗在东宫,颇知其事……
今按,据《旧唐书》卷一一八《黎干传》,黎干任京兆尹在唐代宗大历八年至十三年之间,且下文明言“德宗在东宫”,黎干以下诸事不当置于肃宗名下。《御览》卷七三五(3/3257)本条称:“肃宗重阴阳鬼神之事,或命巫媪乘驷行郡县,为厌胜之术。有祆人王玙,遂以左道为相。代宗亦笃信之,凡所筑,动牵禁忌,而奸人黎干得以左道尹京。又内集众工,编刺珠绣为御衣,既成而焚之,为禳除法,且无虚月。”《旧唐书》“凡有所兴造功役”句前夺“代宗亦笃信之”六字,遂使代宗事误植于肃宗名下。
39. 卷一三三《李晟传》,11/3662
晟乃逾漏天,拔飞越,廓清肃宁三城,绝大渡河,获首虏千余级,虏乃引退,因留成都数月而还。
点校本在“漏天”、“飞越”、“肃宁”下标地名号,意即李晟逾越漏天,攻克飞越,并扫清了肃宁等三城。但《御览》卷三二五(2/1496)载:“晟乃逾漏天,攻拔飞越、廊[廓]清、肃宁三城,绝大渡河,获虏首千余级,虏乃引去。因留成都数月而还。”《册府》卷三五九亦作“攻拔飞越、廓清、肃宁三城”,《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传》称:“逾漏天,拔飞越等三城。”则三城者飞越、廓清、肃宁,点校本因《旧唐书》省略“攻拔”之“攻”,遂致误解原文。又,“首虏”,《御览》作“虏首”,姑存疑。